一项来自多伦多的研究显示:孤独症和多动症应采用不同的情绪干预方式
研究背景
面孔是一种意义非常丰富的非语言性刺激,是人类表达、认知情感的重要工具和途径,面孔识别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技能。面孔作为视觉刺激的一种类型,既遵循视觉加工路径,又有专门的面孔加工神经元进行特异性的加工。人对于视觉信息的处理主要通过两条通道,一是“WHERE通道”,即枕顶通道,主要与物体的空间位置和空间运动有关。该通道中视网膜的神经纤维终止于初级视皮质(纹状皮质,17区),然后与18区和19区的更高级视觉皮质联系,而后视觉皮质又与后顶叶皮质联系形成“WHERE通道”。另外一条通道“WHAT通道”,即枕颞通道,主要与物件识别和面孔加工有关。初级视觉皮质与梭状回、颞下回联系形成“WHAT通道”。在颞下回里,有专门对面孔分析(如性别、年龄、种族、情绪等)的细胞。而情绪的识别与调整,除了颞下回外,杏仁核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普通儿童而言,情绪识别是一项早期发展的社会技能,4个月龄的婴儿就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识别出高兴、悲伤和恐惧的基本表情,7个月的婴儿可以对熟悉或陌生情绪面孔做出习惯性和方向性反应,1岁左右的幼儿就能识别包括高兴、悲伤、生气、害怕、惊讶和厌恶的基本情绪。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以下简称孤独症)和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Deficit/Hyperactivity Disorder,ADHD,以下简称多动症)存在重叠的症状表征与较高的共患率,且他们均表现出情绪面孔的加工缺陷以及情绪调控障碍。研究发现,该缺陷与他们情绪加工网络的改变有关。
孤独症儿童不管是在行为学层面,还是使用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以下简称ERPs)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resonance imaging, 简称fMRI)或眼动的研究均显示孤独症儿童的情绪加工出现明显的异常。有观点认为孤独症儿童可能存在情绪识别的特异性损伤,比如Caron等人的研究认为孤独症儿童对六种基本情绪的识别都存在广泛性的损伤。也有研究显示,情绪识别的损害或缺失是具有选择性的。比如在Humphreys 等人的研究中发现孤独症儿童对恐惧情绪的识别较差,Dawson在关于负性慢波(Negative Slow Wave,简称NSW,是与负性情绪相关的慢波成分)的ERP研究也支持了该观点。Dawson等人发现相比较中性面孔而言,呈现恐惧表情时,普通儿童N300与负性慢波的波幅更大,孤独症儿童未表现出面孔类别的N300、NSW差异,这说明恐惧表情并未引出孤独症儿童的负性情绪。而对于复杂情绪的识别,即便是在临床上也能明显观察到孤独症儿童对嫉妒、尴尬、不屑、傲慢等情绪的识别明显弱于普通儿童。(详细可点击参阅睿宝官网中《自闭症(孤独症)儿童的面孔识别障碍》)
对于多动症儿童而言,不少的研究也显示在情绪识别测试中较正常发育的儿童表现更差。David Da Fonseca 的研究发现多动症儿童非但在情绪识别上,包括在有环境提示的情绪识别实验中也表现欠佳。而Nicola Yuill Jenny Lyon等的研究发现多动症儿童判断面部的情感性信息比判断面部的非情感性信息更困难,因此提出了多动症儿童可能存在特别的社会认知缺陷。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主要探讨孤独症与普通人群(Typical Developing,以下简称TD)、多动症与普通人群之间的差异,如孤独症在面孔加工时初级视觉皮层、梭状回 (FG)、颞上沟 (STS)、杏仁核和岛叶等区域存在非典型激活已得到充分证实;基于血液动力学(Haemodynamic-based)、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s, 以下简称ERPs)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resonance imaging, 简称fMRI)等有关的研究也发现多动症存在情绪面孔加工异常。然而,目前还很少有研究比较孤独症和多动症这两种神经发育障碍人群情绪加工的功能连接模式。
来自加拿大的Safar教授团队使用脑磁图(magnetoencephalography,以下简称MEG),试图确定并比较孤独症、多动症和TD儿童加工不同情绪面孔(快乐和愤怒)时的全脑功能连接模式。
研究内容
(如对研究具体内容缺乏兴趣,可直接跳至“研究价值”阅读)
实验任务:内隐情绪面孔加工任务(Implicit Emotional Face Processing Task)
被试:
最终被试包括100名孤独症(含23名女孩) ,71名多动症(含17名女孩),87名TD(含32名女孩),被试年龄为5-19岁 。
使用韦氏智力量表测量儿童的全量表智商(Full-scale IQ,以下简称FSIQ);使用儿童行为检查表-注意力问题分量表(Child Behaviour Checklist attention problems subscale,以下简称CBCL-AP)测量儿童的注意问题;使用社交沟通问卷总分(Social Communication Questionnaire total score ,以下简称SCQ-TOT)来测量儿童的社交问题;使用适应性行为评估系统的一般适应性综合得分(Adaptive Behaviour Assessment System’s General Adaptive Composite score,以下简称 ABAS-GAC)来测量儿童的适应功能问题。
结果显示,三个组年龄、男女比例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FSIQ、CBCL-AP、SCQ-TOT和ABAS-GAC得分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FSIQ:TD韦氏智力显著高于孤独症和多动症,孤独症和多动症不存在显著差异;CBCL-AP:TD注意力问题显著小于孤独症和多动症,孤独症和多动症不存在显著差异;SCQ-TOT和ABAS-GAC:与TD相比,孤独症与多动症表现出更严重的社交沟通和适应困难,且孤独症比多动症更为严重。
实验材料:
快乐和愤怒情绪面孔的图片,共52张,其中12张为女性面孔。每张图片周围有2cm蓝色或紫色的边框。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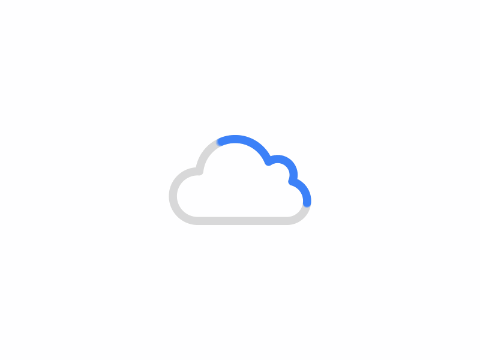
实验程序:
实验包括75%的非目标试次(non-target trial)和25%的目标试次(target trial),其中非目标试次呈现的图片边框为某一颜色(蓝色/紫色),目标试次呈现的图片边框为另一颜色,所有试次随机呈现,每个试次中图片停留时间在300-500ms之间。实验者要求被试忽略面孔图片的情感内容,仅关注图片边框的颜色,并在出现目标试次的边框颜色时,迅速按键作出反应。被试在磁屏蔽室中以仰卧姿势完成任务,同时使用151通道的CTF系统(CTF MEG International Services LP , Coquitlam, BC, Canada)记录其脑电数据,采样率为600赫兹。
数据采集:
- 行为数据:被试在目标试次按键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 MEG数据:为了避免按键动作对MEG数据采集的影响,仅使用在非目标试次中,被试做出正确反应(即不按键,类似“信号检测论”中的“正确否定”)时的MEG数据。
数据分析与结果:
- 行为数据
在目标试次,组别(TD,孤独症,多动症)和情绪面孔类型(快乐,愤怒)对正确率和反应时的主效应均不显著,交互作用也不显著。在非目标试次,组别(TD,孤独症,多动症)对正确率(即不做出按键反应)的主效应不显著,但情绪类型(快乐,愤怒)对正确率的主效应显著,具体而言,在各组中,被试在快乐情绪面孔的试次的正确率比在愤怒情绪面孔试次中的正确率更高。
- MEG数据
1、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
使用MATLAB工具箱FieldTrip对MEG数据进行预处理(Preprocessing)和源重建(Source Reconstruction)。MEG数据通过滤波分成θ(4~7Hz)、α(8~14 Hz)、β(15~29 Hz)、γ(30~55 Hz)不同频段。选择基线状态(-200ms~0)和刺激呈现后200-400ms的MEG数据以及进行后续分析,分析方法为基于网络的统计分析(Network-based statistics, 简称为NBS),该方法可检测各组被试的脑功能网络中哪些子网络存在显著差异。
结果如下:
将年龄和性别作为协变量后,在θ、α和γ频段组别的主效应都不显著,而在β频段组别的主效应显著,事后检验显示,与孤独症和TD组相比,多动症组的平均网络连接强度(mean network connectivity strength)更低;而与TD组相比,孤独症组的平均网络连接强度更低。该网络主要涉及额叶、皮层下和颞叶的连接,主要固定在左半球,其中连接度最高的是左侧额叶中回、苍白球和颞上回。该网络还涉及关键的面部加工区域,包括双侧杏仁核、右侧梭状回和左岛叶,以及与边缘系统、枕部、顶部和颞部脑区连接的眶额区。
在γ频段发现了唯一组别与情绪面孔类型显著的交互作用,具体而言,与愤怒情绪的面孔相比,TD组和多动症组对快乐情绪面孔表现出更多的连接;而孤独症则相反,他们在愤怒情绪面孔下的连接更多。该网络涉及双侧额叶、大部分下额和眶额以及边缘和颞部脑区之间的连接。 大多数连接是在额叶和边缘区域之间,包括右杏仁核、左岛叶和左前扣带皮层(ACC)。双侧眶上和眶中额区和左额下区分别与右上和左中颞极相连;右眶额区和右角回之间也有联系。
2、数据驱动的聚类分组(Data-Driven Subgrouping)
与基线水平相比,每种情绪的主效应作为分组的依据,Calinski-Harabasz指数显示,最佳的分组数量是两个。于是根据MEG数据将被试分为两组,组一包含28名多动症、38名孤独症和22名TD,组二包含43名多动症、62名孤独症和65名TD。两组被试年龄、性别比例、TD/孤独症/多动症的比例均无显著差异,但两组TD和神经发育障碍(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以下简称NDD,在该实验中,NDD包括孤独症和多动症)的比例却存在显著差异,组一NDD比例更高,称其为NDD主导组(NDD -dominant subgroup);组二TD比例更高,称其为TD主导组(TD-dominant subgroup)。
两组FSIQ和SCQ-TOT无显著差异,但CBCL-AP和ABAS-GAC存在显著差异,与TD主导组相比,NDD主导组存在更多的注意和适应功能问题。
对于快乐情绪面孔,在θ和β频段,NDD主导组平均网络强度比基线增加,而TD主导组比基线减少,两组差异显著;对于愤怒的面孔,在α和γ频段,NDD主导组平均网络强度比基线增加,而TD主导组比基线减少,两组差异显著。
- 大脑与行为数据的相关性
在β频段,在多动症、孤独症和TD三组中,平均网络连接强度与CBCL-AP呈负相关(r = -0.236,p = 0.001)。
在γ频段,在多动症、孤独症和TD三组中,愤怒面孔的平均网络连接强度与ABAS-GAC分数负相关(r = -0.244,p = 0.001),而快乐面孔的连接强度与ABAS-GAC分数正相关(r = 0.199,p = 0.009)。
本研究报告的结果表明,多动症与孤独症的不同之处在于,①不管是什么情绪,多动症儿童没有将足够的注意力分配到面孔加工的任务上(在β频段,三组平均网络连接强度与CBCL-AP呈负相关,而多动症组的平均网络连接强度低于孤独症和TD组)。②孤独症组在加工情绪和面孔方面困难更大(在γ频段,与愤怒情绪的面孔相比,TD组和多动症组对快乐情绪面孔表现出更多的连接;而孤独症则不明显)。同时,数据驱动的聚类分组发现孤独症和多动症两个群体作为NDD的相似性多于作为不同诊断组的差异。
研究价值
作为国内较早开展孤独症儿童面孔识别的认知神经心理研究的学者,睿宝专委会的揭晓锋主任(添加微信咨询专家)对研究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既往的研究确实显示了孤独症与多动症儿童都存在着情绪识别的异常,但应该存在着不同的神经机制。不少孤独症儿童对于高兴、生气、伤心、害怕、惊讶等基本情绪的识别存在困难,但多动症却很少出现对基础情绪识别困难的表现,更多地是在复合情绪的识别上存在困难,并且一旦控制多动症儿童的注意力,反复要求多动症儿童将注意焦点回归到情绪图片时,大多数多动症儿童就不再存在明显的情绪识别问题了。Safar教授等人的研究比较两类儿童在情绪识别困难上的不同有着很强的现实价值。正如研究中所得到结论一样,孤独症儿童在加工面孔及情绪上存在着更多的困难,极有可能存在情绪加工的特异性损伤,而多动症儿童在情绪识别上的困难则可能是没有将足够的注意力分配到面孔加工的任务上,而并非存在特异性的损伤。因此对于存在情绪识别障碍的孤独症儿童应该采用系统的情绪识别训练,而对于多动症儿童则更多应该采用注意力训练来改善情绪的识别。”
系统的情绪识别训练主要包括:情绪面孔识别的训练、场景情绪以及愿望情绪训练。
阶段一:情绪面孔识别的训练
1、运用照片识别脸部表情
通过人物照片识别开心、伤心、生气、害怕等基本表情。在开展该阶段训练前,务必确保儿童已经能认识面孔的各成分,比如眼睛、嘴巴、鼻子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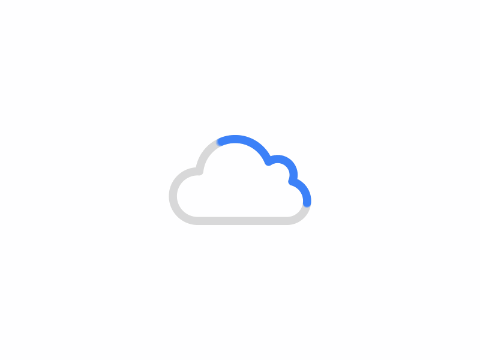
2、运用图片识别情绪
通过卡通和线条画图片识别开心、伤心、生气和害怕四种基本面孔与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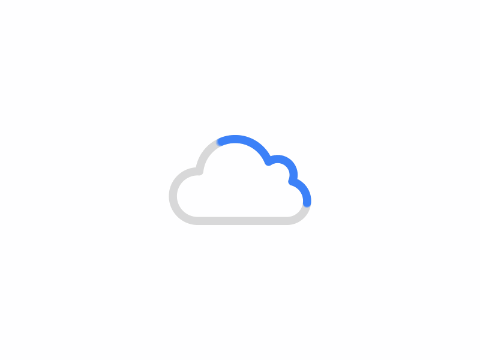
阶段二:场景情绪训练
通过基本的面孔情绪识别后,儿童需要根据特定的情境去预测他人当时的情绪状态。训练需要准备空白面孔的情境,通过不同的情境儿童直接指认主人公的面孔及情绪。进行到此阶段时,需要确保儿童能够稳定认识因果关系。
图 情境情绪图卡:碰见狗时会“害怕”
图 情境情绪图卡:吃麦当劳时会“开心”
阶段三:愿望情绪训练
人的情绪不仅跟情境有关,也跟自身的愿望相连。当现实情境跟愿望相吻合,人就会感到开心;而当现实情境跟愿望违背,人就会感到不开心。在该阶段,儿童需要根据一组图片(愿望图片与现实情境图片)中主人公的愿望满足与否来预测主人公情绪感受。此阶段需持续强化儿童理解情绪的以下基本原则:
- 当我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会觉得开心。
- 当我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我会觉得伤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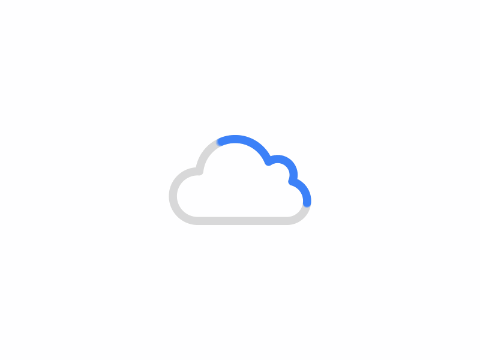
图 女孩的愿望想要一双鞋子,结果妈妈真的给她买了一双鞋子。(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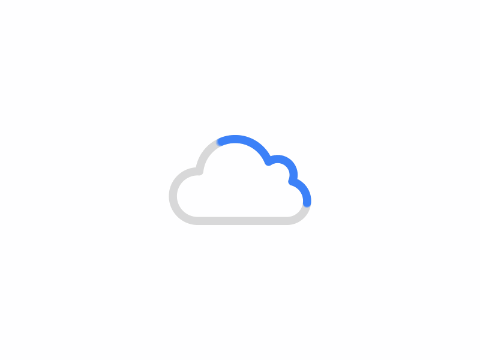
图 男孩的愿望是去海边玩,但爸爸带他去文化公园。(不开心)
该文献的翻译来自睿宝团队,参考文献来自于下方文章,可点击查看原文。
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以及咨询专家,可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服务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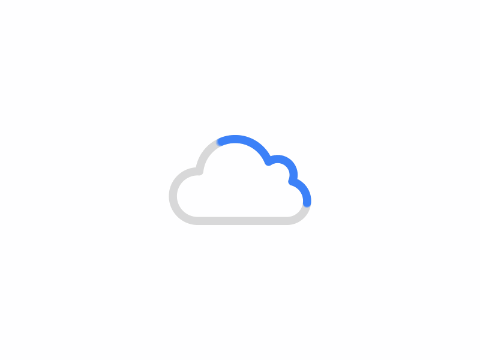

共有 0 条评论